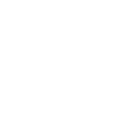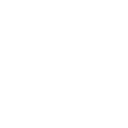半岛官网入口网页版好书推荐丨《潮起》:解开中国创新型企业崛起之谜本书以详实的史料和深刻的洞察,通过对“以市场换技术”和“自主创新”两种企业的发展路径进行对比分析,阐明它们的行动差异,从宏观的政策变迁和微观的企业创新两个层面解释中国创新型企业崛起的深层次原因。书中再现了中国政府和企业在工业追赶和自主创新的历程中披荆斩棘、在曲折中前进、在逆境中奋起的历史细节,令人动容。
本书作者封凯栋在过去20年间进行了超过500人次的个人访谈,受访者包括工程师、企业管理者、工人、学者和政府官员。正是在访谈和调研中的切身感受,驱使作者带着强烈的使命感展开工业研究。
本录中国工业从“以市场换技术”到“自主创新”的艰难转型过程,总结了后发国家进行工业追赶和技术学习的宝贵经验。
书中通过对华为、比亚迪、奇瑞、大唐电信展开案例研究,揭示“工程师主导的权力结构”是中国创新型企业能够实现崛起的原因。
本书文风朴实,文字富有生命力。书中详细讲述“北京吉普风波”“七八计划”“鞍钢宪法”等中国政府和企业在迷雾中摸索、一步一步试错的历史事件,令读者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和民族自豪感。
阅读本书,广大工程师群体及企业的管理者将获得强烈的共鸣,因为书中所讲述的正是他们的故事、是他们所亲身经历的历程。
“新一代青年人”将对中国工业自主创新的历史进程获得更深刻的认识,从而有针对性地提升自身能力,融入自主创新的时代大潮。
公共管理、学、科技政策、经济学、经济学等专业的师生及研究者可以获得第一手的资料,拓展对中国工业政策和创新企业成长的理解。
封凯栋,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长聘副教授、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英国萨塞克斯大学科学政策研究中心(SPRU)博士,清华大学管理学硕士、工学学士。长期从事中国工业和中国创新政策的研究,在国内外期刊发表近百篇论文,出版了Innovation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China和《国家的双重角色:发展与转型的国家创新系统理论》等专著。
与路风教授合著的《发展我国自主知识产权汽车工业的政策选择》及相关的工业研究工作对推动我国自主创新政策转型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曾在中美创新对话半岛.体育 (中国) 官方网站、中国电动车百人会等政府间对话机制和国内组织中担任中方专家和首席专家等角色,是学术团体AIRNET(The Academic-Industry Research Network)骨干成员。
未来10~20年,中国企业都将面对一个不太友好的外部环境。如何在逆境中实现技术突围,《潮起》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答案。
本书从工程师主导的中国自主创新型工业组织的角度,梳理和展示了中国产业崛起和科技创新突破的历程,不仅是对中国经验的真实总结,也是对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诠释与弘扬。
《潮起》所揭示的是,中国创新型企业涌现的必然性来自中国企业对自主技术学习的努力探索,来自决策者在关键历史节点抓住机遇推动的政策范式转型,更来自中国人民长期以来追求自立自强的社会共识和精神面貌。
本书作者长期关注我国创新型企业的发展,在过去20年间访谈了500多人次的工程师、企业管理者、工人、学者和政府官员。正是在系列访谈中的亲身体会,驱使作者带着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去研究创新型企业与创新政策。本书通过介绍我国创新型企业的成长和奋斗历程,告诉读者正是战略层面的坚定信念推动这些企业走上创新之路,而不是跨国公司的恩惠与发达国家的施舍。
(以下节选自本书“引言”的最后一部分,原标题是“写作动机:中国工业和中国工业人的历程”,略有删减)
自从接手了路风教授的“全球视野下的中国工业与经济发展”这门面向北京大学全校本科生的通识核心课之后,每年在课程的第一讲中,我都会给同学们讲述工业研究对于我个人的重要意义。
我本科就读于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大部分大学生一样,我在进入大学之前,几乎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家乡广西。通过高考,我考进了高水平的大学,成为当年该系120名新生中的一员,开始接受全面、繁重且严格的学科训练。
然而,与我们所接受的紧张且严格的训练不相称的是当时工程类大学生黯淡的就业前景。当时,“市场换技术”实践盛行,中国工业对产品开发和复杂技术的人才需求很小。不负责任地说,当时可能是中国的工程技术人才所面临的一段长夜。虽然我们早早就被系里告知,本系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上的供需比是1∶14,意思是每个毕业生平均会有14个用人单位在等待。但这些潜在的雇主要么是体制内已经困境重重的老牌国有企业或科研机构,要么就是中外合资企业或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办事机构。后者通常能提供高于当时中国平均收入水平的工资,但它们提供的职业前景往往是工厂管理人员、质量控制工程师、售后经理、贸易代表、公关经理等。简单地说,它们要的主要是我们所在大学的名头,而不是我们通过四年的艰苦学习所获得的专业知识。
这个“长夜”中的困境戏剧性地反映在毕业生的就业去向上。一方面,我们当中一些毕业生选择出国留学,这部分人可以成为世界知名大学的博士生,然后在发达国家获得工程师或优秀科学家的职位,兑现他们身上的知识的价值;另一方面,在国内相关行业,我们通过努力学习获得的知识似乎并无用处。我在2020年的时候做了简单且不严谨的统计,发现在全年级120名同学中,只有10%~15%的人留在机械相关行业发展事业;更多的人选择离开工程类行业,转而成为跨国公司的经理、金融家、咨询公司专家、码农、互联网创业企业家、政府官员等,他们都能在各自的领域中发挥自身的价值。
虽然我在大学四年级一开始就获得了清华大学新设立的公共管理学院的免试研究生资格,然而彻底改变我志向的则是大四冬天的工厂实习经历。我和我的四个同学去了广东省佛山市一家位于远郊高速公路边上的铸造厂。工厂大概有2 000名工人,大部分是来自湖南、江西、广西、贵州等省份的中年女工。工厂主要生产下水道金属件半岛.体育 (中国) 官方网站,尤其是三通管。工厂经理告诉我们,他们的产品在全球市场都享有盛誉,甚至连纽约时代广场的下水道也使用了他们生产的三通管。
生产过程简单粗暴,高炉生产铁水、铸造、锻造、车削以及喷漆等大部分工艺都需要由工人们手动完成。这批女工几乎是世界上最好的工人半岛.体育 (中国) 官方网站,无论是近距离完成铁水浇铸还是操作机器锻压铁块,她们始终毫无怨言,哪怕完成从铸造到喷漆整套流程,整个班组只能分到2角/件的收入。工厂为工人们提供的生活条件极差,午饭只有糙米、泡菜和猪皮,以至于我们当中一位同学一度宁愿每天步行40分钟下山到公路交叉口唯一的餐馆去吃饭。我们另外四人时不时也会同往。即便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女工们依然有非常高的工作热情。为了获得更高的收入,虽然工厂惯例是早上7点钟开门,但她们在6:30就早早地到达了工厂,希望经理能提前打开车间让她们开始上班。
整个实习过程对于我们来说是无聊的,因为毫无疑问我们的知识对工厂、对女工毫无用处,事实上我们也自觉地尽量不给工人添乱。唯一兴奋的人是经理,他是整个工厂少有的西装革履的人,他每天都热衷于跟我们聊天,给我们传授毕业后为人为商的成功之道。
导致我最终“崩溃”的是结束实习的时候,我个人决定去跟一直沉默相处的“工友们”告别。这次开谈让我意外地发现,工友们的年龄普遍都在16~22岁,很少有人超过25岁。然而,她们的脸却已经被长时间的辛苦劳动雕刻,但她们甚至都不认为自己应该对此有所抱怨。意识到这些人几乎与我一样大让我备感挫败,在另一个场合,我们甚至可能是朋友、同学或玩伴,然而,现实的反差让我不知所措。“一个可能的我(工厂经理)”和“2 000个可能的我(农民工)”之间的强烈对比对我的价值观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终于开始直面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当前的情境下,即便是成为一名工程师也难以从根本上改变这“2 000个(乃至更多)可能的我”的生活。因此,我彻底抛开了机械工程,转向学习公共政策并尝试寻找参与改变现状的可能。而后,当我在2003年收到路风教授的邀请去研究中国工业和工业政策时,我立刻就意识到这就是我想做的,也是我应该做的。
对我来说,参与工业和工业政策的研究是我个人参与中国工业实践的方式,也是我自我实现的形式。这种经历让我更深入地理解自主创新企业的崛起可能为中国经济社会带来的变化。因为本土工业只有持续地升级,才能为更多的人提供体面的工作。
事实上,很早就进入中国的跨国公司普遍在2005年之后才在中国设立研发机构,也正说明了这一点。在此之前,它们主要将中国看作廉价的生产制造资源的提供地和人口庞大的消费市场,只有在华为、中兴、奇瑞、吉利和比亚迪等中国自主创新企业崛起之后,它们才开始对中国的工程技术人力资源进行重新“估值”,才开始利用中国工程技术人员的“人口红利”。这种转变既来自它们受到了自主创新企业组织模式的启发,也来自它们不得不回应自主创新企业带来的竞争压力。
当然,成为一名公共政策研究者并不能直接改变中国工业的面貌。事实上,我的工作主要是将他们的奋斗转化为政策分析语言。从这一点来说,是无数具有“不信邪”“不怕鬼”的创新精神的企业家、工程师和政策决策者共同完成了本书所讲述的历史。这本书的材料基于我从2003年开始,在20年中进行的超过500次的个人访谈,受访者主要是工程师、企业管理者、工人、学者和政府官员。其实,我更渴望将来自己有机会写一本关于自主创新过程中个人故事的书,因为在工作中,我们遇到过太多令人振奋、令人感动或者令人遗憾催泪的人物和故事:
我们见到过东北的老国企,在遭遇巨大的困难时召开了全厂员工大会,最后全体员工一致同意大家利用业余时间自己动手义务劳动去修建新工厂;
研发国内首台万门交换机的科学家,为了获得电子元器件,多次坐绿皮火车到深圳中英街的二手元器件市场淘宝,甚至一度在火车上被人误以为是“盲流”;
1992年,深圳一位电信设备公司的老板站到了公司楼顶,努力说服自己不要跳下去,最终还是勇敢地回到公司去面对困境;
1997年,一位李姓企业家参与了自己企业第一辆车型的设计,但当时他手里的“设计工具”只有游标卡尺;
同样是在1997年,一位参与奇瑞早期创业的骨干,因为被“造车梦”所吸引,决意离开自己的妻儿和稳定的工作从石家庄南下,却在火车开动后突然号啕大哭;
1999年,中国地区发生“9·21”大地震,代表奇瑞到福臻模具公司监督模具开发的一汽退休老工程师,在地震发生的第一时间毫不犹豫地扑到了模具上,用身体来保护企业“自主开发车型的希望”;
2001年,大唐信威的工程师在大庆油田建造了-40℃环境中的基站,因为当时主流市场已经被跨国公司占据,他们只能在如此恶劣的自然环境下才有机会尝试布局SCDMA的网络设备;
2003年,一批华为工程师在香港SUNDAY电信公司的设备机房里打地铺,等待着后半夜利用设备的闲暇时间来调试华为卖出去的第一批3G设备;等等。
年青的一代或许是幸运的,因为“七国八制”“老三样”“新三样”这些名词将离他们远去;在他们成长之初,中国就已经拥有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制造业,这使得他们具有更强大的自信、更开阔的视野去解决未来的问题。但在成长过程中,他们很需要去了解那些在长夜中坚持“不怕鬼”的、最艰难的故事,以此明白中国工业力量的源泉,并以此来明确方向。
在政策辩论中,我经常会被认为是激进的“国家主义者”或者对中国工业创新的前景过于乐观。这种认识并不正确,正如我在前面所提到的,我的旅程起源于自身的困顿与迷茫;在与大量的中国工业实践者接触,了解到他们和他们所在企业的奋斗和成长历程后,我更认识到自主创新的崛起是一个漫长、困难甚至充满了辛酸与失败的过程。可以说,我的乐观来自对民族精神的信心,来自我个人在过去20年的工业研究中所看到的中国工业和中国工业人的韧性。在到达彼岸之前,他们以巨大的付出和忍耐翻越了时间的高山。
也许是10年或者25年,我们有理由在更长的时间尺度上对中国工业和中国工业创新的前景保持乐观。因此,如果我们有能力与更年轻的学生和读者对话,与他们辩论甚至被他们辩倒,都是有价值的。这正如今年“全球视野下的中国工业与经济发展”的第一周课程下课后,一位同学问我,中国经济能否走出当前国际经济剧变下的困境。我回应说,这很可能是你们这一代人的使命。这位同学略带惊讶和迷茫地说:“我们可以吗?”
“生命不怕死,在死的面前笑着跳着,跨过了灭亡的人们向前进。”(这句线年所作的杂文《生命的路》。——作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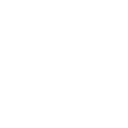

13988886666